南京城墻和羅馬城墻的比較便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即非從結果圖解和剖析它們的不同,而是和城市關聯性的認知揭示發展路徑和走向,這就是“這墻和那墻、這城和那城”的來由。
由此我們發現,當城墻界定了城市范圍時,也界定了一種文化;當城墻投射出城市變化時,也投射出歷史進程。
同質一,城墻作為城市的一個界面,形成相對穩定的范圍:南京城墻始建于公元3世紀,明代將以前歷史遺留城墻進行串聯并擴展成總長35.267公里,圍合城市面積41.07平方公里,外郭總長60公里,形成230平方公里的都城;羅馬城墻始建于公元前4世紀,羅馬全盛時期奧勒良城墻(Mura Aureliane)總長18.837公里,圍合面積約13.7平方公里,作為羅馬帝國的城市,在公元3世紀十分龐大。
異構一,城墻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建立起的秩序是不一樣的:上述城墻圍合的面積差異,也在一個方面表現出同為城市,但是體系不一樣。明南京墻體除城墻外,內還有皇城和宮城,外建有郭城,這樣的四重城形制實質為嚴密加強防御,最中心的部分是皇權所在。在南京的歷史上,從孫吳建業到六朝建康,從南唐加強南部城墻,到明代擴展東、西部和北部城墻,都是為皇帝及子民建立一個堅實的堡壘,并足夠的用地備戰儲糧。而羅馬古城其實是整個羅馬帝國的權利象征,其野心和擴張,表征在以此為發動機,由條條渡槽、棧道和鋪路,將帝國的痕跡通往歐洲的各個地方,建立不同的城鎮實體,而心臟本身之圣城并不范圍廣袤,以合理和可控的管轄。這樣的不同秩序從根本上來自于文明建立的核心理念:中國傳統“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其防御的心理本質上出于山川環抱的地理環境適于農耕和穩定的生活以及產生的文化;而羅馬沿用古希臘“衛城—城邦”體系,每個城市面積不十分大以民主自治,衛城是圣城。明城墻圍合起的南京,代表了中國古代城市內向的、對外設防的城市基本性質和思路,奧勒良城墻圍合起的羅馬,則體現了自希臘傳統延續的、以圣城為主體向外擴展的組織架構和層級秩序。
公元前4世紀塞維安和公元3世紀奧勒良城墻及城門
同質二,城墻建造沿用舊有遺構,變化擴展因地制宜:南京和羅馬城墻都是巧用歷史上歷代城址進行聯系,或加筑加寬,同時根據當時需要善用地形進行建造的。整個城市城墻呈現不規則狀態,順水、架山或聯系歷代城址,都是善用自然和人工的智慧體現。
異構二,城墻的建造內容和功能不盡相同:南京城墻毫無疑問是為了防御,即使是占地面積很大的甕城,如“聚寶門”和“通濟門”,里面有可居的足夠面積,也是為了屯兵,曰“藏兵洞”,城樓和箭樓除了彰顯城市威嚴外,更主要是為登高望遠、觀察敵情和組織御敵。而羅馬城墻除御敵外,通常有些具體的功能,如居住,或者在建造時便考慮將已有的塔樓、營房、金字塔甚至是墓地整合進去,形成可以日常使用的具有混雜性質的城墻。
同質三,城墻建造的尺寸和材料基本相似:南京城墻除架山墻、包山墻,使得墻體和山體融為一體外,在平地上建造的城墻高度大約10米左右,寬度10~20米;羅馬城墻記載高有6米、10米等幾種。反映出出于軍事目的,城墻的基本高度是和人體尺度、御敵方式有關,差異不大。在材料上,羅馬城墻和南京城墻均用磚石進行建造,起堅固作用。
異構三,修繕的觀念和技術路線存有差異:經歷時間的滄桑和風雨的剝蝕,城墻都有待保護,在具體操作上,如南京城墻某些段遵循的“修舊如舊”和“原材料原工藝”原則,與羅馬城墻修復注重“易識別性”(如用區別古磚的紅磚或黃磚)和采用“新材料新工藝”(如涂料和微型綁定技術),有迥異差別。從技術路線看,這樣的不同有著傳統做法的根源,而從本質上看,是對待文物或遺產的觀念不同。20世紀上半葉,文物建筑保護意大利派吸取總結了歷史上的合理理論和做法,于1931年制定的《雅典憲章》和1964年制定的《威尼斯憲章》,均強調反映文物建筑的歷史真實性,著眼于保留文物建筑所攜帶的全部歷史信息,并且“必須利用……一切科學技術來保護和修復文物建筑”(《威尼斯憲章》),代表了西方文物建筑保護的基本準則和意義,也是歐洲工業革命社會條件下的必然結果。我國在1961年制定《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其中第11項指出:文物建筑“在進行修繕、保養的時候,必須嚴格遵守恢復原狀或者保存現狀的原則”。這在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的文物建筑修繕起到指導性的作用。從審美而言,西方注重的真實性和中國強調的真善美,也從文化心理加速不同的修復觀念和技術的分野。盡管當今這兩大派別有交流、有滲透,但在具體實踐中,長期形成的傳統做法和價值取向還是在操作與對策中產生不同的應對,如南京城墻保護十分注重收集舊磚,而羅馬城墻保護對于不斷更新的技術使用始終走在前列。
更多有關建造師資訊的信息請關注我們,在線老師會免費提供試聽學習資料,在線預約可享受課程優惠,點擊進入【百學教育】網站詳細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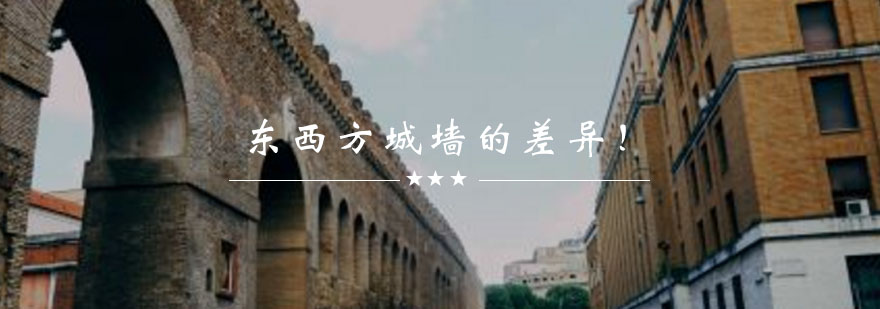








 安全工程師考試有哪些刷題技巧
安全工程師考試有哪些刷題技巧